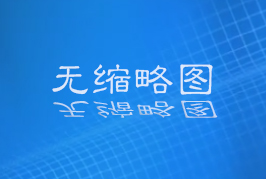法治时空(http://www.ghwshi.cn/):访谈: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
梳理2013年以来发生的暴恐袭击事件,发生地多集中在南疆地区,参与乌鲁木齐、昆明等地暴恐袭击事件的嫌犯籍贯也多是南疆地区。
记者/张弛
新疆是中国反恐的主战场,南疆则是新疆反恐的前沿阵地。南疆不稳,新疆不宁。
一般意义上的南疆,指的是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苏地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降水稀少,沙漠广布,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四地州人均GDP不足全疆平均水平的45%,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疆的85%,农村富余劳动力占全疆的63%。同时,宗教氛围扭曲,周边环境复杂,反恐形势严峻。南疆部分地区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东伊运”等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这里既是反恐维稳的重点地区,也是改善民生的难点地区。
2014年8月下旬至9月初,《凤凰周刊》记者深入南疆乡镇,探访中国反恐的前沿阵地。通过对不同民族、行业、阶层人群的采访,尝试多视角还原严打专项行动下的南疆现状。负责现场处置的阿克苏新和县特巡警大队长姜兆刚,搜捕嫌犯时亲眼目睹爆炸现场尸块横飞;在莎车“7·28”暴恐事件中执行搜捕任务的特警队员卡米力,把当天配发的唯一一瓶水让给了警犬;年过六旬的疏附县乌帕尔镇老汉苏力坦,将迷路的“伊吉拉特”嫌犯引到了村警务室。还有从乌鲁木齐机关下派至喀什乡村的维吾尔族干部,以及负责排查流动人口的汉族社区工作人员。
壹
“在南疆做特警挺危险”
口述:卡米力(莎车“7·28”暴恐事件执行搜捕任务的维吾尔族特警)
我叫卡米力,1992年出生,维吾尔族。我2010年进的喀什特警队,是队里专门负责带警犬的。其实很多维吾尔族人家里不养犬,觉得犬是不洁的东西,养了之后天使不会进你的家。但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犬,是自己申请进的警犬大队。
我带的犬是寻找爆炸物的搜爆防暴犬。警犬能不能训练出来,关键要看品种,不同的犬种适合不同的科目。像搜爆防暴犬,一般都是马犬、德牧和昆明犬,它们的嗅觉比较灵敏,也很凶猛。要训练这些犬,必须从小就带。这些犬来的时候,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两个月,大的也不超过半年。我的犬名字叫辛巴,与《狮子王》重名,今年5岁了。它执行过一些搜爆任务,表现出色。
“7·28”莎车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喀什市,我们平时一般都在那里。到莎车的时候大概已经上午8点多了,事情基本都处理完了,我们就带着犬在警队待命。第二天开始执行任务,主要就是进行抓捕,辛巴也帮忙找到了我们负责抓捕的一些人。我们分了好几个组,我带着辛巴搜房子。如果怀疑嫌疑人藏在房子里,就先让犬进去,进去之后有情况犬就会叫,这样大家都可以提高警惕。
在进屋之前,我们会先在院子里喊话,让他们出来。我们那个小组没遇到有人拒捕,有些可能时间拖得长了一点儿,但也没有反抗。其实,我感觉他们主要是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了,跑也跑不了。
我们小组负责的是荒地镇18村、15村和12村,嫌疑人名单都是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早上出去,除了武器装备,其他就只能带一瓶水。那天天气特别热,搜到村周围的棉花地和玉米地里时,有一条犬中暑了。犬本来就怕热,这种天气我们人还好,它受不了。带的一瓶水,我自己没有喝,全都给了辛巴。
莎车人口有90多万,是一个大县。这边农村确实挺穷的,我进他们房子里时看到过,真正的家徒四壁。农村里一家大概两三个孩子,四五个的也很多。其实那些老百姓99%的人都很友好。你进到老百姓家里,人不在的话可以找邻居,哪怕不认识。邻居会说‘他不在,你是来做客的,不如先请到我的家里来坐坐’。
我从小上的是民语学校,学的是维吾尔语,到大学才学的汉语。学习汉语不容易,语言环境太重要了。以前我们少数民族读大学,不管汉语水平如何,都要先读一年语言预科,这个规定最近两年才取消。我在乌鲁木齐上大学时,汉族同学就住在隔壁,白天一起上课可以学一点,下课以后就到他们宿舍打牌聊天,也能学习。
2010年,从新疆财经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我报考了特警。南疆维吾尔族警察挺多,因为会维吾尔语是优势。这里的人听不懂汉语,我们可以和他们对话。新疆大学生找工作挺不容易的,尤其维吾尔族,我们当特警也是要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我同学,现在当老师的比较多,当警察的有四五个,还有在医院当会计的。我们特警队2010年招的这批,全部都是大学生。说实话,当时报考的时候,我就想着当公务员,进来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么不好干,天天训练真的挺累的,这个工作太苦了。
平时的生活也很枯燥,一天到晚就是训练,每天至少7个小时。一出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家里也照顾不了。收入很低,像我一个月也就3000元,很多来得比我晚的队员,一个月只有2000多元。我们宿舍三个人,一个汉族、两个维吾尔族,平时我们工作吃饭全都在一起。
在南疆做特警其实挺危险的。不过,家里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父亲。父亲以前就在莎车荒地镇工作,2014年3月自治区派了20万名干部下基层,我父亲就主动申请来莎车工作,因为他对这边情况比较了解。
贰
“如果老百姓不配合我们,肯定很难完成搜捕任务”
口述:姜兆刚(参加阿克苏新和县“7·24”暴恐事件现场处置的特警队长,汉族)
我是河南濮阳人,1983年出生,阿克苏新和县特巡警大队的。我们大队主要负责处置突发事件。
2014年7月24日下午6点15分左右,我们接到命令。我立即带了一个战斗小组的特警队员赶到了现场。当时,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带着民兵过去了,我看到的是一个爆炸现场:房子已经着了火,屋外散落着大量的爆炸物,还有一名自爆身亡女人的尸体。屋子里很凌乱,一个小孩的摇篮也着了火。我想,里面可能还有其他人,就带着队员进去搜索。房间很小,也就几平方米。还没进到房子里,一个女的拿着爆炸物就自爆了。
等确定里面已经安全,就请技术人员清理爆炸物,然后我带着队员参加搜捕。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很多,有老百姓、民兵,还有村里的干部。因为南疆的农村都差不多,白杨树、乡间小路,我们也不太熟悉,追也没有方向。后来,有老百姓告诉我们,说往哪个方向跑了。
先是在玉米地里发现了5个小孩。离房子也就三四百米的距离,都是他们丢下的。他们是从后院跑的,拿着炸弹、抱着孩子,估计嫌麻烦,直接就把孩子扔了。
孩子都很小,最小的两个月,最大的两岁半。为了所谓的“信仰”,扔掉这么小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母亲?当时老百姓听到有小孩的哭声,过来一看,一大堆,就抱到自己家里面,报告说捡到了小孩。
这些都是老百姓主动告诉我们的。他们说,看到一群人往哪个方向跑了,然后指点我们追。搜索的区域比较大,那一片主要是棉花地、玉米地和果园,7月份庄稼正长得高,距离远的话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我们副局长带一组,我带一组。农村玉米地里没法开车,一些民兵、老百姓发现线索以后,我们就坐他们的摩托车去追。这不算什么,有一次我们还坐了驴车呢。

农村手机信号不好,电话联系不上,加上又是玉米地,确定方位特别难。这时,在距离我大概100米的地方,响起爆炸声,烟很浓,有20米高。确定了方位,我们赶到现场。现场很惨烈,地上被炸了一个大坑,还有被炸得不成样子的尸体。但我们没时间关注死人,主要看活着的人,看看他还有没有抵抗能力。
我们副局长满身是血。两名暴徒拿刀刺伤了他,胳膊上砍了三刀,腿上也砍了两刀。我们果断开枪,但那两个人还是跑了,玉米地里不好打。我们赶快转移受伤战友,然后继续搜索。那些人拿着刀,根本就不怕,直接就向你冲过来。
我最早是部队上的,后来到的特警支队。来这里5年了,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我觉得那次是比较惨烈的。很多队员回来就把衣服扔了,上面都是血。我没有,挺好的衣服,洗洗接着再穿。你看,现在我这裤子上还有血迹呢,洗不彻底。
新疆现在采取强制性措施,很多人不理解,那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不过,到现场去,如果老百姓不配合我们,肯定很难完成搜捕任务。其实当时老百姓、民兵处境也很危险,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有的是拿着铁锹、拿着棍子,有的就拿根树枝,也在跟着我们一块儿围捕。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如果没有老百姓的话,那场仗不会打得这么漂亮,也不会那么成功。
我现在24小时一秒都不能放松,神经高度紧张。不能听到电话响,就不停地换铃声,这样还能缓解一下。我的电话没有用坏的,都是摔坏的,晚上睡觉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失眠。队员们差不多都这样。我原来90公斤,现在只剩70公斤了。

叁
“只要我活着,就坚决和他们斗到底”
口述:苏力坦(喀什疏附县乌帕尔镇智擒嫌犯的六旬老人)
2014年7月的一天,我听村里大喇叭广播说来了暴恐分子,要大家注意安全。我很担心村里的水源,怕坏人下毒,所以每天都去林子里看一下。那天早晨,我也过去看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就回家了。下午又过去,发现有个人神色慌张地从树林里蹿了出来。
我一看这个人很面生,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就想是不是暴恐分子?我知道那些人很凶残,心里很紧张,怕他会伤害我。但如果一喊,附近也许有他的同伙,到时想跑也跑不掉,要想个办法。我就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让他慢慢平静下来。然后,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他没有带刀具,就开始跟他聊天。我想,只要没有刀具,就是动手,我一喊的话,附近肯定也有人过来。
我心里有数了,对他说正在找自己家的牛,开始慢慢套他的话。他先说自己是巴楚县的。我就问他,有身份证吗?让我看一下。那个人说,没带。我就说,你把身份证找一下。如果你能找到身份证,我就把你送回去。然后那个人说,身份证找不到,你帮帮我,把我送回去。我说没有身份证的话你走不掉。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个人又说,是从疏附县来的。问他哪个乡,他说不上来,最后说他迷路了。
这时我确定,这个人肯定就是暴恐分子。我就说,我带你到大路上去,找辆车送你走。那个人说身上没钱,我说你放心好了,我给你解决。就把他带到了自家门口。不过,我又一想,如果把他带到自己家里,我的家人可能会有危险,就想把他带到村里的警务室。从家到警务室还有一段距离,那个人就不想走了,我就说车在这儿不停,那边才是停车的地方。快到警务室门口的时候,那个人又不想走了。我就说,你是真的想走还是不想走?他说想走。我说,如果想走的话就跟我过去。那个人就跟我进去了,然后村警把他抓了起来。
我今年66岁了,是20多年前来到这个村定居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我的100亩树林子里大概有3万多棵树,有好多人想买我的树,但我不打算卖。现在我年纪大了,这个树对儿孙都是有好处的。你看我们这个环境,上面都是沙子,为了保护水源,防护林也不能砍。政府很关心我们,在这件事上一直鼓励我,所以我坚持了下来。
我这辈子没当过干部,以前是做木匠的,五个儿子也都是木匠。儿子们没有培养出来,但我的孙子孙女们,我都要让他们上大学。我想让儿子给我买个手机,以后遇到可疑的人、暴徒什么的,可以随时打电话报警。只要我还活着,就坚决和他们斗到底。我们要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宁,平平安安过日子。
(后续:根据这名“外乡人”的交代,当地警方联合地方政府,组织了干部、民兵和民众计200多人,分四路进行搜索,在一个山崖上将其他5名嫌疑人抓获,并在他们携带的包里搜出了食品、攀登绳、手电、药品、刀具等物品。经审讯,6名嫌疑人均为“依吉拉特”组织成员。他们打算从乌帕尔镇越境,如果不成功就地“圣战”。)
肆
“我们下基层,工作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不是以我们为主”
口述:匿名维吾尔族官员
20万干部下基层,我是第一批,2014年3月5日去的喀什。我出身干部家庭,这样的事情要带头。原定时间是一年,但这个一年,到底是指2015年的3月5日还是2014年年底,没有明确说法。南疆是按到2014年年底执行的,比如那些从地区、县上下去的干部。
我是自治区厅局的,直接下到村里边。两年前我自己去挂过职,是村长助理,这次去,我们副局长才相当于村长助理。厅局级干部到下基层任村长助理,你看看这级别降了多少?这次我们下去了两个副局长。
我在北疆长大,北疆和南疆差别真的很大。我家在伊犁,那个地方受俄罗斯影响较多,而且地域辽阔、水土丰茂,只要种东西就能有收成,不像南疆。农民把种子一撒,就听天由命了,该干啥干啥,很轻松的,所以北疆的文化娱乐什么的,都比南疆要发展得好,就是因为这边的人空闲时间多。南疆那边农民就是干活干得多,还没收成。
伊犁的文化是各种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中亚几乎所有的民族,包括俄罗斯族、犹太族等等,特别多元,在这里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小时候上学,一个班里都有好多个民族。我的汉语是到北京读内高班以后才学的。
地方政府对媒体一般都避而远之,因为它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错。大家都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错,其实哪个地方正确它也知道。反正它越避着你越好,最好外面人什么都别知道,自己说啥就是啥。其实这才是真正能够触及深层次问题的。我们有时候也下去调研,明明有好多东西都不对,但我们不能说,怕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就这样了,改也改不了。如果要改的话,从上到下、从头到尾整个体系全都得改,不是说这一个地方这样,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这样。
我们下去,当地老百姓都很欢迎。干部对我们一般敬而远之,工作组毕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督促他们改进作风嘛。再说,我们的职务是啥,村长助理,想见个副乡长都不容易。不过,如果局长想见,他们会过来的,这就是角色转换嘛,很快的东西。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是不通情理,像这里的书记、乡长其实都经常过来,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说,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尽量帮助他们解决。
但我们毕竟不是当地的干部,有些事我们也解决不了。像资金问题,如果乡里面哪个项目缺钱,我们肯定想办法支持。你缺个文化广场,我给你建文化广场,你缺商店我给你盖商店。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都可以帮忙干。但有些事不行,比如农民分地的问题。我们手里没有地,农民要地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还有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把人家房子强拆掉了或者是把地拿走了没给钱等等。我们能做的,是帮他们反映情况、协调关系,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地党委政府。
我们办不了他们能办的事情,只是协助他们办事情。下基层,工作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不是以我们为主。这也是自治区党委对我们的要求,“好人要让基层干部去做,好事要让基层组织去办”。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帮老百姓做几件好事,更重要的是帮助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有句维吾尔谚语说得好,“水会流走,但石头会留下来”。我们会离开,但我们离开的时候,希望能看到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基层组织。
像你说的那些收钱办事的,我觉得喀什这边还稍微好点儿,最严重的地方其实是和田。和田人卖玉石,有钱,所以一个护照在和田能炒到20万元。我现在所在的麦盖提县,在南疆经济条件不算最好,但稳定情况还不错,文化产业比较发达。很多人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抵御极端思潮,我觉得这只是偶然因素。当然不发展不行,但发展得好也未必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像莎车的“7·28”事件,其实就发生在麦盖提县和莎车县的交界地,但别人都觉得是莎车乱。
在这里我并不感到害怕,怕的人是因为他没真正下来过。因为不了解情况,心里总有些顾虑,觉得是民族聚居区,可能不知道哪里扔来块石头就把他给砸了。我们工作组7个人,6个汉族,就我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也有这种担心,这很正常。虽然都是新疆人,也在这里长期工作,但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区情,有些人甚至连南疆在哪儿都不知道,去了一看都是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肯定心里发毛。其实要是真正融入进去,和老百姓交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伤害你?
和田那边可能形势要紧张一点。和田人和喀什人还不一样,和田人特别犟,拗得很,你要得罪他,他早晚要跟你算这笔账。如果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但你只要对他稍微不好,他会加倍报复你,这就是和田人的性格。我听说那边村与村之间都有隔离带,有的村里面也设了卡。
这里吃得还行,就是住得有点紧张。我们住在村委会大院里,网络设施也有。为了保护我们,晚上村干部和村民都会到村委会值班,还有几名协警,每天都十几、二十几个人。院子里有些没墙的地方,我们就把墙补上,然后拉上防盗铁丝网。
我担心的是,当政府越来越努力、越来越成功的时候,民众反而会感到压力。像去年我到县上办事,街上就有无数的警车来回开,警笛拉得特别响。每天都这样,就那么一两个小时,不停地闹。而且很多武警都是从内地调来的,他们不懂少数民族的风俗,有时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跟当地人发生误会。

伍
“社区排查工作量很大,天天加班加点”
口述:匿名社区女干部,汉族
我在社区工作,是临时聘用的,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你说在乌鲁木齐怎么生活?这边收入都不高,社区干部也就3000元。没办法,只能出来开出租,趁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挣点儿钱补贴家用。现在上面有了新精神,要求同工同酬,但还不知道具体落实起来怎样。
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送信息。在新疆基层工作挺不容易的,因为反恐维稳,活儿干得比谁都多,天天加班加点,有时候还不被人理解。晚上入户,经常被人骂。值守公交站点的,查包认真了,有时甚至被人打。一旦辖区出事,还要倒查责任,社会上骂的也多。可恐怖分子脸上又没写字,混在人群中我们也分辨不出来啊。
我们在社区工作的,还要求必须入户普查基本资料,所有人都要去。比如一个小区,一栋楼有24户,这24户的基本信息采集,都由一个人负责,诸如常住人口有多少、流动户有多少、家里的重要成员等等。主要是针对流动户,因为牵涉到房屋出租,可能三天换一个人。常住人口,只要资料齐全,就不怎么反复查。
只要有事发生,就开始排查,大多也都针对流动户。我负责的那个片区,靠近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人员构成复杂。很多南疆来的人,基本都在那儿租房子,短的有时只住一个星期。排查的时候,一般是8-10人一组,有派出所的跟着。一些比较危险的临时住户,有时我们不敢进去,就叫上巡逻队的人一起进去。
排查工作量真的很大。那边的房东为了多收租金,都把一套房子隔成好多个格子。后来,我们让他们把隔板拆掉,安全隐患太多。比如火灾,走的线安全隐患特别明显,我们全部强行拆掉。新疆大学、科技大学都在那边,租房的还有些大学生,男女混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有时我们去排查,那些女娃娃穿着吊带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先去把衣服穿好。这些学生,我们排查几次,他们也就烦了,后来都去别的地方住了。
我们想,这样排查租客不是办法,还是要找房东,让他们提供出租人的照片、身份证、合同、房产证等资料。但有些房东根本就见不到人,找他他也不来。像这些事情,内地哪有啊,都是一辈子都不跟他们打一次交道的那种。但我们这边的社区,什么都得管。

我们单位少数民族挺多。现在社区干部,还不如保洁员,一个保洁员每月还能拿到2000元。我觉得政府对维吾尔族照顾太多,住房、工作什么都紧着他们,还给他们发这个发那个。就这样,人家还不满意,一天到晚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