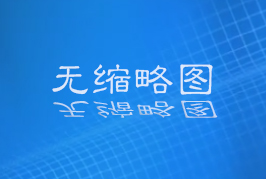法治时空(http://www.ghwshi.cn/):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 兼谈学风问题
过去,本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给予过关注,首次在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是在2000年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谈到影响美国20世纪初发展的思潮部分。
我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概括起来是: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去,美国就不会有今天,或许早已引起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经济崩溃。事实上,另一条线,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在。它也是植根于美国的思想传统之中,也就是自由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强调平等这一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同时,在经济、哲学、政治领域都有其对立面,不过在特定的时期哪一派成为‘显学’,视情况而定”(《冷眼向洋》第41页)。
在详细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改良思潮和批判运动以后,本书又引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一段话:“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第89-90页)。我在那本书里的着眼点在于说明:促使一个社会的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平等的关系。显然,在最适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生长的土壤的美国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遑论其他国家!
本文不是要介绍这部著作,或讨论美国的发展道路,而是阐明我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之所以想到要就这个问题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主要原因是近来读到和听到一些对当前国情的描述和观点,实在不能苟同,感到有话要说;又由于在有些人那里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比较混乱,最近还听说海外有人把国内的“自由主义派”与“里根主义”等同起来。另外还曾有人把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加于我的头上,也正好借此阐明观点,立此存照。
我所指的不能赞同的那类观点就是现在被称为“富人经济学”的种种说法,其内容包括夸大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缩小贫富悬殊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侈谈正在进入小康社会、强调贫富悬殊是发展必要的代价,甚至腐败和专制都是现代化必要的代价等等。关于贫富悬殊问题,我原则上不反对一段时期的贫富差距是发展的必要代价,我们是在短缺经济下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穷过渡”之后进行补课。
但是这种差距能促进发展得有几个条件:
一、财富的集中基本上是通过合法途径,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
二、集中起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掉或流失海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转移,不是投资);
三、贫富差距有一定限度,不能超出无法忍受的地步,也就是所谓“警戒线”,而且有积极的缓解和制约机制;
四、弱势群体有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揆诸我国现状,这些条件都十分欠缺,而且在有些方面向相反方向的恶性循环还在变本加厉,看不见转向良性循环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年前已经不同,人们平等观念已大大加强,有横向比较,一百年前能忍受的不平等,今天就难以忍受。所以今天的中国既患寡又患不均,社会的不公正正在制约发展。至于说腐败也是必要的代价,我更不能认同。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过腐败无害论,并举国外发展的阶段的数字与腐败的比例加以论证,当时我就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孳生腐败的土壤实在太肥沃,现存体制又只能助长,难以遏制。时至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无孔不入、弥漫性的腐败已经不但腐蚀社会的肌体,而且在咬噬内脏,触目惊心。我仍然坚信,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那种为了保护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宁愿付出腐败的代价也要维持专制的说法。另一方面,与另外一些论者不同的是,我认为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和深圳等特区的繁荣不能代表全国,是显而易见的。有些问题与一些熟透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来相似,成因却是不同的。即使有一些是从外面传染来的,也是由于自己的痼疾太深,对外来影响只能取其糟粕而无力吸收其精华。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文不是要在学理上全面评价斯宾塞所提出的学说。这里只就通常一般的理解而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通过生存的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这种规律的运用至少有很大的局限性。关键在于它的大前提:机会平等、规则一致。
在自然界,客观条件对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以及各种天灾,大家都同样经受,于是有的被淘汰,有的顽强地存续下来,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至少在进入“文明”之后,很难有完全平等的条件。就以美国为例,假如说第一代移民白手起家,相对说来机会平等的话(其种族歧视问题此处姑且不论),到第二代就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因为家庭背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机遇就已经出现差别。正如接力赛,第一棒在同一时间同一起跑线上,优秀者跑在前面,而第二棒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因此,以到达终点的时间来衡量最后一个接棒人的优劣显然不公平。这是最简单化的比喻,社会的发展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果听其自然,历史越悠久就越不平等。60年代美国终于通过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后,为保证其实施又通过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法令。约翰逊总统针对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反对这一法令的意见说过一段话:“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年带鐐而跛脚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同别人竞赛了”,正说明同样的道理。所以即使完全铲除了世袭贵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靠宪法规定给予一切人以平等的权利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必要条件,还需要一系列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形形色色的福利制度。
至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现在离相对的机会平等也还差得远。最明显的,天天可以看到的,北京城里几百万“外地”打工仔、打工妹,就不享受与北京市民完全同等的权利。占全国人口起码三分之二的农民在有形的经济、社会福利上,或是无形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同城里人也远远没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唯一的还算公平竞赛的全国高考(舞弊的不算),大批失学儿童和少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出局了。在法制不健全、权力的作用处处可见的今天,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享受到平等机会,达到真正优胜劣汰的机率还是很小的。再深一步说,姑且承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则,这“强”与“弱”、“优”与“劣”的标准是什么?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上强者就是体魄健康加聪明加勤奋,弱者不是太笨就是太懒,或者体弱、病、残。但是在一个贿赂公行、腐败成凤的地方,一个既聪明又勤奋的人如果坚持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就生存不下去,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问题是由这样的环境来“选择”“适者”,社会能进步、民族能优化吗?
过去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用“所谓”,是因为我不认为那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绝对平均主义并不体现机会均等,在本质上不公正的,而且它掩盖了实际上的各种金字塔式的特权。在短缺经济下,极少数人所享受的各方面的特权与广大无权无告的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同今天的贫富差距哪个更大,很难比较。不同的是,那时是静止、僵化的,今天是流动的,希望在流动之中。事实上,今天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并非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仍然是旧制度改头换面,以各种形式阻挠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老的大锅饭的残余造成庸才压制英才,扼杀创造性的现象与新的两极分化,使弱势群体处于无权、无助的状况,两种现象在现阶段是并存的。要达到健康的、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毕竟,社会在动荡中前进,不是死水一潭。不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的严重性,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困境,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此处不赘。本文只是想简要说明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得出中国缺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论。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我一向不把自己归属于哪一派,而只是就问题论问题。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我与一些人的观点相同,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许正好与另一些人巧合。不过我从不讳言,在大的取向方面,我认为源于欧洲的关于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以及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法制、民主的一系列原则是有普适性的。就广大中国公民而言,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种种挫折,这个启蒙过程尚未完成。“自由主义”当然包括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到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证明自由竞争与平等二者不可偏废。在实践中往往产生矛盾,太侧重平等,则导致削弱竞争意识,不利于发挥创造性,今天的北欧国家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反之,则两极分化难以遏制,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动乱。欧美国家根据自己各自的国情,在总的“自由主义”框架下不断左右摆动,调整政策。欧洲称作“左”派和“右”派的,与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内涵和外延就不尽相同。里根主义对当时的美国功过究竟如何,至今美国人争论不休。中国国情如此不同,任何比附只能是牵强附会。在今天的我国,既不能以发展为借口而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也不能因当前的弊病而否定改革,主张倒退,更不能重新肯定那腥风血雨、导致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几乎切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文化大革命”。
前面提到被误加以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据是一份称作《新左派评论》的英文杂志2000年第6期刊载了一篇访谈录,由汪晖先生概述中国知识界的各派观点,其中涉及本人的一段如下:“几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场关于两极分化的大辩论,有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一些年轻一代的思想者把目前的潮流描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和资中筠回答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即不适者生存”。
有人把此文印给我看,使我大为惊奇,这是根据何来呢?上述《冷眼向洋》中的内容是我唯一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而且只联系美国,从未涉及过中国。文中还用了“大辩论”和“回答”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辩论,本人没有参加过,更从未与汪先生讨论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文中没有直接引号,也没有任何出处。我曾问过李慎之先生,他也矢口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有过这样的想法。当然本文只代表我个人。究竟汪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通常的做法是,见到后立即致函该杂志予以正误。我当时没有那样做,因为正在全力写另一部专著,实在懒得为这种无聊的事分心。另外,我潜意识里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不愿把中国人之间的分歧拿到洋人那里去评判。而且本人白纸黑字的著述都在,一篇“访谈”也没有那么大影响。我尽管工作一直在“国际”领域,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己明确的定位是主要为中国读者而著述,除参加国际讨论会必须提交外文论文外,我的写作绝大多数是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的。我在意的是中国读者的反映,重视的是与中国学者交流思想,因为我念兹在兹的是本民族的兴衰,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关心和担忧的是“士林”的状况。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有热心友人告诉我,传给我看,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份杂志和这篇英文“访谈录”。不过这倒真促使我开始注意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议论,作进一步的思考,现在那本书已写完,可以抽出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关于这方面的看法。说不定哪天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谬种流传开来,也可有此存照。
最后,还想说一点学风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抄袭、剽窃进行了很多揭发和挞伐。把别人的思想、写作据为己有当然很不道德,此风应该大力刹一刹。但是,反过来,把自己的杜撰公然加到别人头上,如西人俗语:“把话放到别人嘴里”,这应该算什么呢?去年,我碰巧也在国外被要求就中国当前知识界的思想作一演讲。我首先表示,我没有能力做这样大的题目,因为对每一位学者来说,如果没有认真读过他(她)的至少部分的著作,对其观点作概括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全面的评论,只有作为专题,认真、系统地大量阅读、分析研究之后才有资格作,现实中很难有人能做到。我能做的,只是就我的阅读和交谈范围所及,谈一点我注意到的对当前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看法。我没有举任何具体的人名,因为手头没有可资引用的文本。我想这样做比较谨慎妥当。
我的精力、时间有限,只想以有生之年就自己“思”与“学”一得之愚写一些想写的东西,对于见诸报刊的争论,即使是本人感兴趣的问题,即使涉及本人的,我一般不参与笔战。到这把年纪,所遇到的多属晚辈,甚至隔代人。关于他们,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治学的遗憾后说:“晚生于我的学子,少年时有一段失学,基础较差,但是机会来时仍然凤华正茂,有志者还来得及补课,施展的天地也要(比我的时代)广阔得多,当然又须经得起新的‘世风’的诱惑和考验。我仰慕前辈的学养和积累,自叹望尘莫及;又羡慕后辈的精力和机会,感慨时不我予”。这是真心话。
我只希望风华正茂的学人们珍惜大好机遇,以“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善用自己的才华和精力,则士林幸甚,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