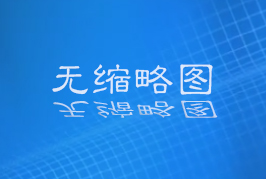法治时空(http://www.ghwshi.cn/):罗志田: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未获得共识
原标题:罗志田: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迄今没有获得共识

罗志田教授
教育的宗旨,到底是要造就人才,还是要培养合格的人,从晚清起就一直在讨论。按中国传统,读书人有化民成俗的责任,学问与社会本是一种关联互动而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大学是一种引进的外来体制,伴生的是大学对社会的责任观念。在一个分工的社会里,若大学完成了其所谓的本职工作,应当就算承担了它的社会责任。 但什么是大学的本职工作,又是一个迄今没有获得共识的问题。大学如何做到既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又不独立于社会,这其中的分寸感如何把握?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最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一书,对这一系列问题有自己的思考。
澎湃新闻:您不止一次提到过鸟多树林才会有趣,为什么现在大学的包容性越来越差了?社会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
罗志田: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基本想法是,任何群体性的机构或领域,多元永远比一元好。从“五四”以来,中国读书人一直想要打破的,就是学术和思想的一家独尊状态。在当时人看来,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形成了一家独尊的倾向。其实孔子最著名的主张就是“有教无类”,其门下甚杂,已为同时代人所注意。子贡认为这是孔子“修道以俟天下”,故“来者不止”。后来《说苑》更借《诗经》中的生物学思路论证说,先要柳树繁茂,然后蝉鸣汇聚;有渊深的潭水,才有芦苇的丛集。所以,“大者之旁,无所不容”。后人所说的“有容乃大”,或者就是从这来的。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就明确提倡要兼容并包。虽然不一定做到了,至少从生物学视角看,体现出一种健康的倾向。中国传统主张“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就是从观察生物界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学问。我常看“动物世界”一类的电视节目,里面宣扬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对异己(the other)遵循一种尽可能“共处”的取向,最利于生存。如果树林里只有一种鸟,不仅没有趣味,还可能影响树林的整体生态。一种鸟独占树林的结果,最后可能是那种鸟本身的灭亡,而树林也随之俱亡。所以,各种声音都有的树林,不仅更有趣,也更适于生存和发展。
要说大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确实如您所说,是越来越不好了。理论上大学不存在包容社会的问题,可能更多是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产生出相当多的不满。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以前中国的读书教书,基本是民间的个人或家庭行为,政府主要负责以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验收”。从晚清引入新教育,这格局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一些基本原则,到现在也没能釐清。如教育的宗旨,到底是要造就人才,还是要培养合格的人,就是从晚清起就在讨论的问题。由于定位不清,结果可能是两方面都不成功。
民国前期的人对外国思想了解更多后,越来越认识到新教育的一个趋势是资本主义化。山东一位长期从事教育的读书人王鸿一就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扩充教育是为了发展实业,知识也逐渐商品化。随着新学校体系中老师越来越把教书当成职业,学生自然也把求学视为获得资格以求职业的手段。老师教书成了“劳动”,要按劳计酬,学生则是出钱买资格。结果是“教以利, 学以利”。获利成为影响教育的一个核心观念,于是“高尚之精神事业”就“变为交易市场”了。或用蔡元培的话说,“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贾之买卖”。这就严重腐蚀了师生关系,而学生背后是实际出钱的家长,他们也就是那对学校有各种期待的“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
按中国传统,读书人有化民成俗的责任。所谓文德与民德,或学问与社会,本是一种关联互动而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大学又是一种引进的外来体制,我们可能也从产生大学的地方引进了大学对社会的责任观念。在一个分工的社会里,若大学完成了其所谓的本职工作,应当就算承担了它的社会责任。但什么是大学的本职工作,又是一个迄今没有获得共识的问题。大学与社会相互的定位非常重要,如果大学的定位是产出能找到工作的人,它的本职工作就是灌输知识和技艺;如果大学的定位是提高民族甚至人类的智慧和修养,那它在教学之外还需要进行今人称为研究的工作,且不止是研究。如果把大学定位成社会的文化中心,它恐怕还要承担以前化民成俗的重任,那就又不一样了。
进而言之,大学除了它本身的教学研究等专职工作外,是否还需要,以及需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同样是个未获共识的问题。我想,只要大学还有“提高”的一面,师生学习的场所就应与“社会”有所疏离。如果校园不能相对独立于社会,失了远虑,必生近忧,恐怕也就难以培养具有“恒心”的超越性人才了。另一方面,今天要把大学设想为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已是一种不可能的迷思(myth)了。且学术既然可以影响社会,就不能拒绝社会的关注,有时还需要社会的关注。其间的分寸,可能真需要全社会的人都解放思想,做进一步的探讨和釐清工作。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学术与媒体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尤其涉及抄袭、学术腐败时)不负责任,哗众取宠,记者素质堪忧;媒体人觉得学界乡愿气息浓重,许多不端只有在外界舆论施压下才有可能得到重视和解决。您觉得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吗?
罗志田:现在学术与媒体的关系应该说不是很好。我们社会对媒体的定位,好像就是他们应当不了解也不懂得大学和教育,而媒体人在这方面也特别愿意配合。我们常常看到媒体朋友关于大学的提问和批评,好像是真的外行,而不像是曾经在大学校园里生活过几年的人。现在我们比较提倡“有特色”,很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就表现出一种特色,就是他们都特别敬业,在其位就不再有出位之思。当其以媒体人身份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忘了“我是谁”,因而往往可以选择性地忘掉自己的经历,以适应社会对媒体的定位。
我们的媒体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大学优缺点的普遍认知,比如好的老师上课一定会用新讲稿,要说老师上课不认真,就会说老师用纸张已经发黄的讲稿(其实现在好多老师都不用纸质讲稿了)。又比如说,很多人爱说老师所教的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也不是学生需要的,不能帮助学生提高学识和技艺。最有趣的是,媒体通常还会把这种固定的答案放到被采访者的嘴里。我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大二的学生指责其老师用的讲稿发黄、知识老化,不适应时代的需要。那后面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大二的学生已经知道本专业需要什么知识,也能够判断老师是否给予了这种知识。这当然有点违背常情,否则那学生就可以直接做教研室主任了,但这恰好符合习见的陈说,而且还鲜活生动,就被电视台欣然播出。
但我不认为这是您所说的“记者素质堪忧”(您或许自我批评意识太强了点儿),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已形成某种固定的机制或套路。我们现在有时也可以看到电视上播出某传媒大学学生毕业多少周年的聚会,那里面的媒体人都说老师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甚至说老师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等等,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但同样是媒体人, 在报道大学教育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出现上面说的情形。
可以设想,如果这个电视台的记者、编辑或者说主播真的是在大学里认真学习的人,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在大二的时候对本专业学术程度的了解没这么深,不足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且我相信他们也知道,中国的大学不是只有传媒大学才好,其他很多大学应该也不错;老师也不是只有传媒大学的才肯帮助学生,其他大学也有很多愿意帮助学生的老师。但是他们在以“公共人”的身份批评大学的时候,就忘掉了作为个体人的自己,忘了这一个体人也曾念过大学。所以我不想说这是记者“素质堪忧”,很可能确实存在一种行业的习惯性表述模式,这种套路化思维至少强化了媒体和学术界的隔阂,使双方的关系渐离渐远。
至于媒体的其他批评性报道,尤其是涉及抄袭、学术腐败的批评性报道,我个人觉得是有帮助的。媒体代表社会,有责任关注学术是不是腐败一类问题。其批评越有建设性,帮助越大。我承认学界中的确存在乡愿气息,很多人不愿意得罪人(我自己也不愿意)。但由于上面所说的媒体特色,有时这类批评显得比较外行。也有一些时候,媒体的批评的确不算很负责任。我理解媒体之间也有竞争,有时为了引起更多的注意,可能会说一些比较过的话。同时现在的媒体好像跟以前不一样,或“社会”对媒体的要求不同了,媒体对报道的准确性,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认真负责。自己出现不准确的报道,通常也不做什么纠正,而是选择自我忘记,也希望读者和听众忘记。当然,我也充分理解现在媒体受到各式各样的压力,有些批评性报道无疾而终,可能也不是媒体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们的学术的确表现出“腐败”的倾向,而且确实已到“严重”的程度。但我并不认为所谓的学术腐败只有在外界舆论施压下才有可能得到重视和解决。现在舆论的压力往往导致上级的批示,更多落实在学校管理者的身上。实际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每一位学者自觉的约束,形成一个健康的学术氛围,鼓励正当的竞争,同时也确立学问的权威。在开放透明的基础上,学术作品和人的学问好不好,最好还是学问做得好的人说了算,而不是由领导说了算,也不是通过以多取胜的所谓学术民主来决定。这个想法可能有些迂腐,算是我的梦想吧。通常说的学术“腐败”有两大类,一是钱财方面,一是抄袭等不端行为。后者依靠的其实就是那些已经疏离于学问的领导以及做得不够好却又总在抱怨的人。真正认真做学问的人,不太容易“受骗上当”。
尽管现在学术与媒体的关系不是很好,我倒不觉得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我不是说现在大学什么都好,没什么可批评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大学的现状很不妙,而且可能变得更不好。但媒体的报道和批评更多是上面所说套路式的,而不见得说出了问题所在(可能看到了没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还是像有些套话说的,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大家都更加主动地承担自己分内的责任——学者把学问做好,媒体人在言及学术时尽量显得内行一点。这样或许就是电视上常说的相向而行。